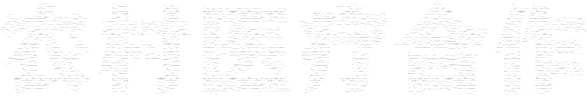1965年6月26日,毛泽东就医疗卫生工作发出最高指示,批评卫生部为“城市老爷卫生部”,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。之后,中国农村建立起一支关注农民初级保健的医疗队伍——赤脚医生。

20世纪的70年代,农村医疗合作在中国进入一个鼎盛时期,全国赤脚医生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500多万人,其中医生180万,卫生员350万,接生员70万。赤脚医生对改变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和农村落后的卫生面貌,对开展预防工作和促进农业生产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20世纪80年代后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,导致合作医疗制度瓦解,1985 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%锐减至5%,至1989年,继续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行政村仅占全国的4.8%。“赤脚医生”也因此失去了政治与经济的依托,部分转变为个体开业者。

根据当时的报道,中国有102万乡村医生,其中近70%的人员为初、高中毕业,近10%的人员为小学毕业。赤脚医生掌握有一些卫生知识,可以治疗常见病,能为产妇接生,主要任务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根除传染疾病。说到接生,就必须一提赤脚医生中‘她们’的身影。在家是掌上明珠的她们在特殊年代也毅然决然挑起这一份责任。

秀芬
秀芬是名接生医生,父亲就是当地的老医生,13岁秀芬中学刚毕业就回到家里跟着父亲学医。年轻的时候,她时常在想,自己何时才能像父亲和罗医生那样,成为一名真正的救死扶伤的医生?往后从医几十年间,她接生上千数,成为了谭坝村的“送子娘娘”。
秋菊
姜秋菊没有非常明确的医生梦,1996年高中毕业时学校组织职业技能培训,她想去“红医班”学习些基本的护理知识和技能,以便将来自我保护;从红衣班到卫生站实习时师父孟医生很是严格,却也时常夸秋菊的胆大心细,秋菊敢走夜路敢打蛇虫,她只觉得自己胆子是比普通女生大些,但那时候她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个好医生。